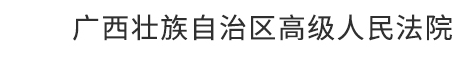案例:广东的蒋成安想到广西买几株桂花树,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恭城县的俸裕华,俸裕华自称有3株树龄在50年以上的桂花树可以卖给蒋成安,其实这3株桂花树全是其唐兄俸裕斌的,由于俸裕斌常年在外打工,因此该树也暂由俸裕华来管理。随即俸裕华带着蒋成安去看树,蒋成安看后非常满意,当即与俸裕华签订了购买合同,合同约定,蒋成安十天后到俸裕华处取树,价钱为每株5万元,共计15万元。合同签订时蒋成安并不清楚该树的真正所有权人是谁,俸裕华也未告知其唐兄俸裕斌有关签合同一事。就在合同签订后的第八天,俸裕斌从外地回来,俸裕华随即将卖桂花树一事告知于俸裕斌,俸裕斌听后非常不高兴,称他的树按现在的市价至少值10万元一株,因此不同意将其卖出。就这样,待蒋成安第10天前来取树时,俸裕华称由于桂花树是其唐兄俸裕斌的,自己无权处分,不能将树卖给蒋成安。蒋成安多次与俸裕华协商未果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俸裕华赔偿因其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3万元。
该案由于合同在签订时俸裕华为无权处分人,依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即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无权处分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后,合同自始有效。但笔者认为,将此类行为定位于效力待定合同,虽然保护了财产关系的静态安全,但未能兼顾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保护,也未能充分保护权利受让人的利益。效力待定的观点有违妥当,可以说是无效说与有效说的简单折中,将合同效力的困扰抛给了“利害关系人”,忽略了许多问题和隐患。更重要的是,它与我国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在理论上不能保持一致,故仍有加以完善的必要。笔者现就无权处分合同问题作一些探讨。
无权处分是指无权处分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的处分行为。所谓无处分权人,就是对归属于他人的财产没有权利进行处置或者虽对财产拥有所有权但由于该财产上设有某种负担而对此不能进行自由处分的人。无权处分,除法律特别规定外,不生处分的效力。对此,世界各国的立法与理论并无分歧。但是这里的“不生处分之效力”应如何理解?其是否包括因无权处分所订的合同亦属无效,还是仅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由于各国对处分的理解不同,其对无权处分所订合同的效力认定也大相径庭。
在当代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理论中,对处分行为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债权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不承认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概念,无权处分所订合同一律无效。这以法国、日本民法为代表,如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规定:“出卖他人之物品者,无效。”以买卖合同作为原因的所有权的变动完全依据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来判定,只要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成立、生效,则标的物的所有权当然发生转移。第二种是公示要件主义立法模式,无权处分场合中的合同是有效合同,但如果让与权利的人对财产无处分权,则其实施的动产的交付与不动产的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这一模式为瑞士、奥地利、韩国等国家的民法所采用,如瑞士民法典第963条规定:“不动产登记,须依不动产所有人的书面声明作成。该所有人对该不动产须有处分权。”瑞士民法典仅仅要求让与人在进行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时须有处分权,而并不要求在订立合同时即具有处分权,即订立合同时让与人是否有处分权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第三种是物权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无权处分情况债权合同有效,但物权行为如不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处分人取得处分权,则属无效行为。这一模式为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采纳,如德国民法典第185条第2款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为有效。2、在后两种情形,对标的物有数个相互抵触的处分时,则只有最先的处分为有效。”这里的处分是专指物权行为而言,并不包括债权合同。
在我国,多数人认为我国目前所采用的是公示要件主义立法模式,但从合同法的条文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是参考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例,但德国民法典所言“处分”仅指物权行为而言,是指在无权处分情况下物权行为无效,并非指债权合同无效。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合同法参照的是德国民法典的立法例,结果却是背道而驰地赞成了法国法的立法模式,即虽然是效力待定合同,但如得不到所有权人的追认或未取得处分权,债权合同亦无效。这一结果显然是与我国在物权法中对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相矛盾的,结合上述案例,有以下几点不妥之处:
1. 效力待定合同显然不利于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和交易秩序的维护。在本案中,合同没有经过权利人俸裕斌的追认并且在事后处分人俸裕华也未获得授权,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该合同应是无效的,确切的说成为自始无效的合同。这就会导致相对人要求处分人赔偿损失只能是基于缔约过失的法定理由,而无法根据违约责任来要求处分人承担赔偿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上是针对信赖利益的赔偿,较违约责任的期待利益其补救性弱,因此,不能很好的起到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2. 本案中是蒋成安与俸裕华签订的合同,然而却由一个合同外的“第三人”俸裕斌去确定合同是否生效,这使得合同打破了相对性原则以及合同为当事人双方合意的本质。一般来说,无权处分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清楚其最终能否取得追认或取得处分权,而受让人往往并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因此,合同双方在合同订立伊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尽管受让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明确的违约责任或者担保责任,但最终却可能因合同无效而使这些违约责任或担保责任一并落空。在该案中,被告俸裕华为无权分权人,他想在俸裕斌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蒋成安作成这笔生意,之后再与其唐兄达成一份购买协议,进而获取差价,如果依照现有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就算俸裕华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他还可以利用其主动地位故意促使合同无效,从而逃避违约责任或担保责任的承担。这对于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很不利。
3. 我国合同法明确确立了出卖人的瑕疵担保义务。合同法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51条规定:“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标的物不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150条规定的义务。”第152条规定:“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这些法律规定确立了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违反了该项义务,出卖人承担的乃是违约责任而并不是导致合同无效。因此,若规定了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制度,那么,对存在权利瑕疵的买卖不应作无效合同处理,而应由出卖人承担债务不履行的相关责任;若不规定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制度,那么,依合同无效来处理前面的所述的案件是适当的。在实践中,总则优先于分则适用,但我国合同法将这两种责任同时适用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情形,这不但影响了条文之间逻辑的连贯与一致性,而且很容易造成当事人对判决依据的误解。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出卖人在缔约时尚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情况,这对于出卖人来说,可以达到融通资金、减少市场风险的目的,也符合市场经济的操作规律。如果立法将此类合同一律认定为效力未定,则无疑会使当事人承担合同目的落空的风险,使交易处于不稳定状态,必然会给交易的正常进行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合同当事人为了防止合同目的的落空,就不得不慎重考察对方当事人是否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是否能够取得处分权,或者真正的权利人是否会对其进行追认。且不论这种考察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是否过于苛刻,即使这种调查是可能的、现实的,也势必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进而导致交易效率的降低,这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权处分合同应当为有效合同,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合同定位于效力待定合同值得商榷。如果设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权利人对处分人可通过侵权请求或合同缔结予以解决。权利人主张侵权,要求返还原物,则处分人在返还原物的同时对相对人承担“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即可;不要求返还原物,处分人向权利人进行侵权性质的完全的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