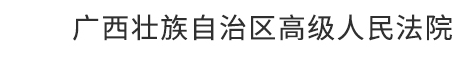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案情】
某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注册股东有五个,分别为原告翟某和被告叶某、顾某、吴某、某纺织公司。其中,翟某出资40万元,持有投资公司20%的股权。2004年3月12日,翟某因个人原因提出把出资入股投资公司的资金作退股撤资处理,投资公司予以同意,双方为此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投资公司在2006年4月前退还40万元入股资金。
2004年3月16日,翟某与四被告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翟某以20.3万元将40万股权中的10.15%股份转让给叶某;以5.124万元将2.562%股份转让给顾某;以7.588万元将3.794%股份转让给吴某;以6.988万元将3.494%股份转让给纺织公司。对付款期限各方未商定,事后也未补充约定。同日,投资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四被告分别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购买翟某所持公司股份,并于2004年4月修改公司章程办理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此后,投资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退还40万元给翟某,也未通过法定程序减资。四被告也未依约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翟某。2010年5月26日,翟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叶某支付股款20.3万元、顾某支付股款5.124万元、吴某支付股款7.588万元、纺织公司支付股款6.988万元,并要求四被告支付从2004年3月16日起占用股款的利息。
被告叶某、顾某、吴某、某纺织公司共同辩称:四被告分别受让翟某股权应付的股权转让款,按《协议书》约定应由投资公司到2006年4月退还给翟某。故翟某主张的债权是投资公司欠翟某的债务,与四被告无关。投资公司未在2006年4月前按《协议书》约定退还40万元给翟某,翟某也未请求履行,其迟至2010年5月才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裁判】
兴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翟某与四被告的股权转让有效,四被告负有依约向翟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翟某在《协议书》向投资公司行使40万元股份收买请求权,实际上是一种减资行为,应当受到公司减资制度的约束。投资公司与翟某在《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免除四被告履行义务,翟某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时,也是请求四被告承担责任,故应认定翟某没有同意债务转移给四被告的意思表示。基于公司减资与股权转让两者的性质明显不同,应认定投资公司在《协议书》中向翟某作出的退款承诺,与四被告受让翟某股权事宜没有关联。四被告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债务人,没有脱离《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关系,仍需向翟某承担责任。股权转让协议对四被告的付款期限未予约定,四被告可以随时履行,翟某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翟某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翟某要求四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叶某向原告支付股款20.3万元、被告顾某向原告支付股款5.124万元、被告吴某向原告支付股款7.588万元、被告纺织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款6.988万元,驳回原告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是一起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纠纷。审理的难点在于对翟某与投资公司所签《协议书》中关于投资公司向翟某返还40万元出资约定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及受让人的义务
四被告与原告翟某均为投资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的规定,四被告与翟某自愿就翟某所持投资公司20%股权的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合意具有可履行性,故四被告与翟某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即为成立。该合同的签订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投资公司章程关于转让主体、受让主体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合同标的亦为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缔约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书》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投资公司为受让人办理了相应手续使四被告分别取得翟某的股权份额,从而承继翟某原来在投资公司的股东权益,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东变更登记,将公司股东的变更向社会作出了公示。据此翟某已完全脱离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退出了投资公司,全面履行了股权转让人交付股权的合同主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四被告负有向翟某按合同约定数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二、关于《协议书》所涉投资公司于“2006年4月前退还40万元”给翟某约定性质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通过对投资公司与翟某所签《协议书》来探究缔约双方的内心真意,应认定投资公司与翟某在《协议书》所作“2006年4月前退还40万元”的约定,对翟某与四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而言,既未构成合同债务承担,也未构成第三人代为清偿。理由是:
(一)从缔约主体看,《协议书》的缔约人只有两个:“甲方”为翟某,“乙方”为投资公司。讼争各方对此并无争议,法院应予以确认。基于《协议书》的“乙方”并不包括四被告,故可认定《协议书》仅是作为股东的翟某与投资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而非投资公司各股东之间达成的协议。
(二)从合同内容看,《协议书》没有表明翟某与四被告就股权转让主要条款达成了合意。通过比对翟某与投资公司于2004年3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和翟某与四被告于2004年3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可以发现,两份合同的缔约日期仅相差四天,《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早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四被告在两份合同上均已签名、盖印。由此,可以推定四被告不仅完全知晓翟某与投资公司于2004年3月12日签订《协议书》之事宜,也应当知晓《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倘若四被告与翟某在2004年3月12日已经就翟某20%的股权由四被告受让之事宜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四被告完全可以在《协议书》中就此合意予以明确。但《协议书》没有明确记载有此项合意,四被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足以佐证有此项合意的补强证据,故不能认定四被告与翟某在《协议书》中已就翟某20%的股权分别由四被告受让达成了合意。
(三)债务转移作为免责的债务承担,须有债权人明确的同意。该同意是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行为,如债权人不同意,债务让与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承担履行责任。本案中,投资公司与翟某在《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免除四被告履行支付股款的义务,翟某向法院起诉主张其债权时,也是请求四被告承担责任,故应认定,翟某没有同意债务转移给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本案并未构成免责的债务承担。与翟某相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仍然是四被告,并未转变为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并未真正成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并不享有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四被告的合同债务没有转移给投资公司,四被告没有脱离《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关系,仍需向翟某承担还款责任。四被告辩称股东债务已转移给投资公司承担,在债权人翟某否认的情况下,仅以翟某与投资公司所签《协议书》不足以证明四被告债务已书面或口头约定由投资公司偿还,四被告对债务转移的主张属举证不能。
同时,《协议书》的内容也未表明各方当事人已达成三方协议或投资公司与翟某达成双方协议或四被告与投资公司之间有共同约定,由投资公司加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关系中,与四被告成立连带关系共同作为连带债务人对翟某负责,故本案可以排除债务加入,亦未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
(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由第三人向债权人清偿。但第三人清偿是以自己的名义清偿他人债务,故于清偿时应向债权人说明。本案中,投资公司在《协议书》中承诺“2006年4月前退还40万元”,并未表明是投资公司向翟某作出“以投资公司名义清偿四被告债务”的明确说明,四被告与翟某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也未作出“四被告债务由投资公司向翟某清偿”的明确约定,因此,不能认定两份合同包含有第三人清偿的内容。倘若将投资公司在《协议书》作出的承诺视为第三人自愿履行,更表明投资公司与翟某、四被告并没有达成转让《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方合同义务的协议。在投资公司代为清偿的情形下,投资公司仅系债务履行的辅助人,并未消灭四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地位,投资公司并未成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或新的债务人。从《协议书》的履行情况看,即使投资公司有为四被告清偿合同债务的意思,投资公司也未实际履行以消灭四被告的债务,据此应当认定,四被告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债务人,仍应向翟某承担责任,翟某有权请求四被告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的规定,实际上《协议书》涉及翟某向投资公司行使40万元股份收买请求权的内容部分,是一种减资行为,应当受到公司法上公司减资制度的约束。基于公司减资与股权转让两者的性质明显不同,应当认定,投资公司在《协议书》中向翟某作出“2006年4月前退还40万元”的承诺,与四被告分别受让翟某股权及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没有关联。
三、关于未定付款期限合同履行期限的确定
四被告与翟某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四被告付款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故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合同补缺性方法的规定,各方未能就此达成补充协议,结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上下文或交易习惯亦不能推知、确定该价款支付的履行期限。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来确定本案债务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根据上述规定,四被告可以随时履行,翟某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与四被告以履行义务的合理宽限期。必要的准备时间是法定期限,即使当事人约定不成也不能否定其存在。故翟某要求履行之日并不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不存在迟延履行及逾期利息的计付问题,翟某于2010年5月26日就《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债权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对原告要求四被告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数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除利息部分外,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