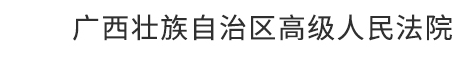2012年12月4日,申请执行人某国土资源局向某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责令某镇某村15、16、18队交出土地和清除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决定。同年12月14日,某市法院参照最高法有关通知精神[1]探索实行“裁执分离” 强制执行模式,作出行政裁定:对申请执行人某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和清除地上附着物及青苗决定准予强制执行,由辖区县级政府组织实施。2013年1月17日,该政府依法院裁定组织力量对案件进行了强制执行。
但在政府组织力量对案件进行强制执行中,法院和政府面临以下问题难以把握:
(1)对妨害执行行为如何处理。执行过程中若出现群众阻挠执行,对阻挠执行的人员,是由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妨碍公务进行处置,还是由法院以妨碍执行进行处理?如前文案例,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有部分村民出来阻挠,蓄意抗法,对这些人员该如何处理?
(2)对违法执行行为如何救济。若政府执行行为违法,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是否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寻求救济?对违法执行造成的损害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还是请求司法赔偿?
(3)对执行后的矛盾化解、稳控等延伸工作由谁负责。若群众就征地补偿安置等问题上访信访,是政府还是法院负责做好接访、化解矛盾纠纷等后续工作?
(4)执行现场监督由谁负责。法院应否派员到场监督?
对上述问题该如何处理,目前法律上还是空白。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是对政府执行行为进行准确定性。而对政府执行行为如何定性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将政府实施的执行行为认定为司法行为,理由:政府依法院裁定这一“司法依据”实施执行权,并非法律、法规授权,无法律渊源。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政府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此,从法理上来说政府的执行行为仍是司法行为。
另一种观点是将政府实施的执行行为认定为行政行为,理由: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 是管理权。一旦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具体强制执行手段的实施则不涉及判断权的行使,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权。因此,政府的执行行为不是司法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对上述观点,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支持将政府实施的执行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理由如下:
一、政府实施的执行权是经司法审查“同意”的行政权。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组织实施的行为,其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司法行为是司法机关实施的行为,其实施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既然“裁执分离”,法院作出裁定是司法行为,符合其司法审查中立角色;政府实施执行则是行政行为,符合其行政管理角色。笔者倾向于实施主体论,即行为实施方为司法机关(法院)的为司法行为,反之则不是。鉴于政府执行依据是法院裁定,非法律授权或委托,笔者认为,此执行权是经司法审查“同意”的行政权,而不说是司法“赋予”的行政权。
二、定性为行政行为有理可据。最高法于《规定》之后下发的《关于认真贯彻执行<规定>的通知》第七点提到“……对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认为强制执行过程中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依法受理”。 且“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最高法《关于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依法妥善办理征收拆迁案件的通知》中也有规定。最高法的上述文件明确无误的将政府执行行为认定为行政行为。
三、定性为行政行为有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将政府执行行为定性为行政行为更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政府统筹协调各部门解决征地后无地农户生产生活的安置及被征地农民的社保和低保等民生保障问题,消除农民顾虑,减少上访信访事件发生。政府作为公权力机构,其掌控着巨大的行政资源是完全能胜任此工作。具体执行工作由政府实施能充分发挥其政治资源优势,同时也减轻了目前基层法院的执行压力。
综上,笔者认为,将政府实施的执行行为认定为行政行为,符合行政主体要求,符合最高法相关文件宗旨要求。
界定好政府的执行行为,前文提到的问题便有了相应解决对策。前述案例的执行,就是在“政府执行行为即为行政行为”理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而且,案件效果良好。在该案的执行中,对阻挠执行的人员由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置;对群众认为政府实施强制执行违法,可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关于执行监督,除由检察院及人大、纪检等相关部门代表现场监督外,法院也派员到场监督,确保了执行工作依法有序进行;对执行后矛盾化解、稳控等延伸工作,由政府协同有关行政部门具体负责,避免了之前由法院执行,群众要求法院解决执行后的补偿安置等问题而法院又无法解决的尴尬局面;执行至今,未发生群众上访信访事件。
【注释】
[1] 最高法于2011年5月6日下发《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文中提到探索“裁执分离”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的模式。文中案例是某市法院对该通知的贯彻执行,首次对农村集体土地非诉行政执行案探索“裁执分离”执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