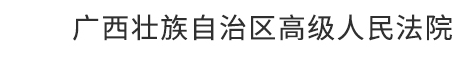什么是法律的理想?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这方面,古希腊人曾有过颇为丰硕的论述,诸如公正与秩序等。但当公正本身以及其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问题时,这些抽象的概念就更显得扑朔迷离了。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其颇为广泛的论述中却极少涉及到这一点,也许,这在中国士人们看来根本就不该是个问题,至少不是个紧要的问题。可能正是这些思想为深入人心的实用主义哲学提供了土壤,又或者反过来深受后者影响,这些就是法律的工具主义本质观。
当我们考查“法”字、“律”字的起源时,会发现其公平如水、均布之义也用来指代法律,这就表明“法律”一词本身就是一个人们不懈追求的品质——公平正义。如同给子女起名字一样,中国古人已将他们对法律的憧憬或法律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应然性嵌入法律的姓名之中。但关于公平的各个侧面及其缘起却缺乏进一步的解释,为何如此?其重要原因就是世俗王权的强大和神权教义的缺失,将世俗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推向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地位。
上古时期,刑或起于兵、或起于祭,都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诸如“受命于天”或“以德配天”,以此来证明立法的正当性。虽然神秘,但其主要基础并不全部来源于宗教,因为宗法制下的王权和伦理秩序仍然是把各个氏族和整个血缘社会紧紧维系在一起的主要手段。因此,当昏昧渐除,民智渐开,人们对神权法的抛弃并没用想象中艰难。即便在“铸刑鼎”、“铸刑书”的年代,最激烈的反对理由也仅是“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一切与神无关。“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对实在价值的看重排斥了法的先验性,当法律的神秘主义薄雾渐渐透露出理性的曙光,也就为人们拒绝法律找到了与天意无关的理由。此时人们讨论更多的是如何有效维护社会秩序,而诸如公平与正义等已不再是跟秩序对等的概念了,它们不过是维护秩序下的一种基本手段,而并非最终追求,自然在哲学讨论中也无需多费笔墨。
以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篇传世判词为例,案情是某甲与妻离婚后,其妻因事犯罪,妻请求用儿子立下的功劳为自己抵罪,某甲怒而不许。判词开篇即阐明大义“二性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鸟岂忘于返哺?”继而陈述案件事实“旋观怨偶,遽抵明刑。”后文则不厌其烦地多处用典,向当事人反复诉说“王吉去妻”之义、“母兮鞠我”之情,言辞恳切,说理性强,用心可谓良苦,因而深受后人赞叹,有称“真老吏判案,若金粉淋漓”。但反观通篇,虽文采飞扬,竟无一字涉及法律适用和法理明晰,至于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及是否适格也仅含蓄晦涩地隐藏在各种文学典故之中,全篇文体用四六格式,对仗工整,与其说是判决文书不如说是道德规范、纲常伦理的“劝谏书”、“劝世文”,法律反而成为了台面下的陪衬。历代被传为佳话的判词大多都是喻情说理、博采华章的文学杰作,但至于法理论证则语焉不详。
白氏的判词颇具典型性地表明中国士人不太关心法律的本体和未来,在他们看来,法律不过是礼教之后的不得已手段。由此古代立法思想也就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即重实效,轻法理。实效的取得并不完全依靠法律,其他手段在短时间内甚至比法律更为有效,如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在立法和司法上表现出任意性和随意性,如商鞅认为刑法的理想状态是“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不过失。”——也就是惩治所谓的思想犯,这种滥刑的主张虽然加强了君主的统治权威,却也当然地破坏了刑事犯罪的法理基础。古代司法裁判的理想即建立社会阶级各安其道的大同社会,但法律本身已是不得已手段,更遑论法理思辨、关系推理和抽象总结了。
当各家学派不再关注法律的本来意义和未来形态,只想最大限度发挥其“兴功惧暴”的功能时,也就留给了司法裁判者偌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不必过多考虑法条的适用与推理。这种朴素的法律价值观导致法律适用的模糊和司法裁判的人治模式,也使民众对法律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感,与其诉诸于法,不如诉诸于官。这种文化基因是中国古代迟迟不能形成一套系统法学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一格局已随着清末修律和西方近代法学理论的引进而有所改观,但传统的影响并未全部褪去,深入人心的观念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这一点或许值得我们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