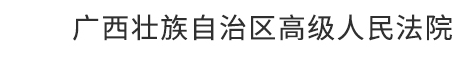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运行,受贿时下已成为一种易发性的犯罪。据统计,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行贿犯罪案件1562人,同比上升60%以上。相对行贿而言的受贿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行贿者被追诉的少之又少,一些基层法院几乎近几年都没有办理过行贿案件。从源头上来看,改变对行贿罪的不平衡责任追究机制,对遏制受贿行为的发生尤为重要。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环节难以界定,多数犯罪嫌疑人以“送礼”为名规避“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实。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送礼之风关乎道德品行,我国刑法没有明文禁止,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及时、有效的起诉行贿者,扼杀受贿罪的萌芽。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2012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司法解释:“行贿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诉”的规定,行贿罪的1万元量刑起点高于受贿罪的0.5万元量刑基准,造成了公诉机关无法全面打击行贿的罪犯,使得一些不法之徒游离于法律的边缘,给司法部门带来执法尴尬。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该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中提到的“边缘被告人”制度,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即“政府为取得某些重要的证据,或者为追究首恶分子的严重罪行,对同罪或其他案件中罪行较轻的罪犯作出承诺,如果他们能够提供某些关键性的证据,将不再对其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刑法立法的基本目的是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只是一种震慑手段,其本质在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正义,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明显的走着“打击受贿为主,侦破行贿为辅”的传统办案路线,为了严惩受贿行为,纯洁干部队伍,常常对提供主要线索的行贿人员采取“马放南山”策略,导致了很多行贿人员只要承认自己的行贿事实,最后就一律得到了宽大处理。如同台湾刑法提到的“窝里反证人”一样,将行贿人当做证人对待,从立法精神层面上说等于是在放纵犯罪。
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是一种组合式的犯罪,然而两罪在我国刑法中的处罚机制却不平衡,实践执法中也是“一头重一头轻,一手紧一手松”。为了解决行贿犯罪成本过低的问题,平衡行贿罪的刑事追诉机制,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处理:
首先,深入研究行贿行为模式的特点,从立法层面平衡对行贿罪的责任追究机制。行贿行为具有目的隐蔽性和手段多样化的特点。目的隐蔽性在于行贿人脱离了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拿货”的功利模式,从行贿行为开始那一刻起就计划这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回报”越晚则“利润”越大。对受贿人而言,“兑现”越晚则风险成本越低。行贿的手段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开展,已呈现出多样化的应对形式,新的行贿手段层出不穷。例如常年承租农家小别墅宴请高官,购名牌衣服委托快递公司急宅送,给领导孩子送名校“入学证”,赠送官员亲属“工作实习机会”等等,都是在和本来已不够严苛的行贿罪责任追究机制打“擦边球”,玩文字游戏。针对行贿行为的新特点、新方式,司法机关的取证能力必须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先行一步。在立法层面,我们可以引入公诉机关提供初步线索,后续举证责任倒置的英美法系模式。从刑法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看,行贿者具备证据上的信息优势,一旦行贿者矢口否认行贿事实,那么证明责任转嫁于公诉方,明显有失公平。例如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第二十四条就对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同时,加强官员的道德品行修养,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行贿的对象是领导干部,行贿的目的是利用他人权力攫取经济利益。要从源头上杜绝行贿罪的发生,必须要提高官员的拒腐防变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保持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行贿者处于有礼送不出去的尴尬地位,从根本上预防行贿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