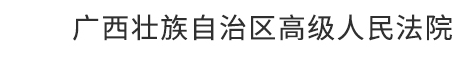在中国,借钱与还钱,可以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身在此山中,或许未有觉察,即使有所苦恼也是哑巴吃黄连,不可言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笔者最近看到一位外国人对此所作的描写分析,虽然文章所写的人与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今天看后仍觉得深刻透彻、妙趣横生。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来华,旅居中国四十余年,并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他深入检讨了中国人在社会性金融活动中的过失。
明恩溥发现,农历新年之前,中国人面孔上总掩饰不住焦虑和着急,雇工会向外国雇主提出增加当月或下月工资的要求,这是因为春节之前会有一个还债期。雇主开始会有所怀疑,而跟踪了解急需用钱的实情后,发现某一个案并不具有特殊性,其他人也身处同样的境遇。为防止雇员因即将面临的灾祸而影响工作,外国雇主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作出让步。
由于中国独特的生活水平和经济体制,金融储备仅能维持有限的余额,所以几乎人人都需要借贷,我欠你的钱,他欠我的钱,形成三角关系,债权人同时也是债务人。过年之前,全国的清偿活动达到高潮,每一个个体既要尽力追踪欠他钱款的人,又要尽力摆脱向他讨债的债权人。因为一笔款如果今年拿不回来,就只能拖到下一年,这样意味着还可能有“下下一年”,谁也无法预知结果。等待的过程,精神备受煎熬。
中国人认为,新年时候讨债,不成体统,不吉利。但是由于身兼债权人和债务人双重身份,左右为难,不讨回钱款,如何过年?于是,农历十二月,就进入一个讨债的高峰,每家店铺,无论营业额大小,都雇佣跑腿人去催债。但是到了大年初一,即使债权人与债务人相遇,大家也不会提起欠钱和追讨的事情,只会说些吉利的话。但是也有例外,有的人大年初一早上仍提着灯笼去讨债,因为据说点着灯笼证明太阳还没有升起,仍属于昨天(去年),还可以讨债,这样就可避开讨债的禁忌。提着灯笼讨债,虽说看似荒诞,有自欺欺人之嫌,却属无奈之举。讨债人如果拿回钱款,欢欣鼓舞自不在话下。欠债人如果通过周密计划成功躲过追逼,同样充满强烈的喜悦,因为迈过了这个坎,就意味着欠款又可以推迟12个月还,得来一个喘息的时间,重新回归平静的生活。
借钱难。明恩溥分析说,中国人借钱有个特点——被迫出借,就是通过施加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压力来达到借钱的目的。在家庭或者宗族内,如一成员欲向另一成员借钱,自己不开口,找一个辈分比后者高的人作中间人提出借钱的要求。借出方一般难以拒绝,明知钱款难收得回来,碍于情面,也只能吃哑巴亏。长辈的权威地位与话语权,使得他们无法不借。在家族之外,借钱就比较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还可以通过朋友出面施加同样的影响。如果这招不奏效,则亲自上阵,给出借人又是磕头又是诉苦,一把鼻涕一把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对出借人来说,也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虽非自己的意愿,也不得不借。明恩溥得出结论说,“不论何种阶层的中国人,一个愿意出借的人也是一个必须出借的人”。
还钱更麻烦。民间有语,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虱子多了,被咬得麻木,也不知道痒了;债多了,反正也还不起,干脆破罐子破摔,也就不用忧愁了。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死皮赖脸的心态。明恩溥发现,人们在受到催促、逼迫之前是断然不会主动还债的,另外,非得催促无数次,否则同样不会还债。即使愿意还债,也是每次只还一部分,剩下部分他会承诺在“第3个月”、“第9个月”或“年底清偿”,可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天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呢?西方人观念上认为,“既然迟早要还,最好是早还”,可是中国人却截然不同,他们的想法是“如果非还不可,也是越迟越好”。“中国人会紧攥住他的钱财不放,直到有一种力量克服他的把持而将它夺走”。这令明恩溥十分吃惊,他在书中感叹说,我们(西方人)宁愿牺牲很大的利益,也不愿意被人催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