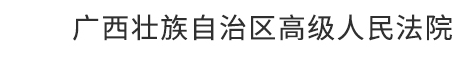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问题的解决,归根溯源又回到了法学教育上。法律教育的核心是实践,而法律教育又是实践最有力的助推器。对此,我国著名法学家沈四宝深有感触,他指出“法律的真谛是实践,实践是法律发展的核心。”可以说,法律的生命并不一定在于逻辑,而在于实施。然而,法律要得以良好地实施,必须要有“像法律人一样思考”的法律思维。培养良好的法律思维则应成为当前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培养法律思维?
改进法律语言在法学教育过程中的运用。法律思维的载体是法律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语言(包括文字、口头、行为上语言)让我们知道发生什么、去思考什么、要表达什么。不同角色,就有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语词,就有不同的思维。 作为法律人群体,在我们的思维中,法言法语经常贯穿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我们在学习法律过程中,其法律思维的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就涉及到法律语言问题。但是正如有位学者所说:“语言就像空气,无所不在,因为人人都用,往往就忽略了它的复杂性。”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像重视法律条文、法律适用那样重视法律语言本身,导致法律语言出现了诸多瑕疵,例如法官作出的裁判文书欠缺说理、事实认定一概而过、法律适用模糊不清等问题。毫不直言,我们学习法律,实际上就是学习法律语言及其使用,要如何去熟练地运用法律语言。不然光懂法律如何如何规定,不知道怎么去使用,那也是做无用功。而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认可直接从这些法律语言而来进行评价,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明不明晰,也可从此管窥一见。
改进法律语言,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依法说理,也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在法律的话语系统内对当事人进行说理。当然,我们在说理的过程中,也要讲求一定的话语技巧,诸如法官穿着法袍(物质性的语言形式)使用法言法语主持双方当事人在法庭里对案件进行调解。法袍、法槌、国徽及其法官所说出的语言共同营造出一个能够充分展示“法理”和讲理的环境。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精英化法律人,除了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之外,还须掌握基本的法律语言理论和运用法律语言的技能。也就说,法律人不仅要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下足功夫,还要在法律语言的书面文字、口语表达及其行为方式上进行改进。 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规范法律语言的使用,促使法律人将更为公正、透明的信息客观地体现在法律文书等载体上,祛除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不信任感,进而拉近彼此的距离,提升司法的亲和力。
强化法律教育中法律思维的理论和实践学习。作为法律人,特别是法官,其所具备的法律专业技能应包括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娴熟的法律解释和分析能力、严谨的法律语言表达能力等。因此,法律教育的方式应着眼于培养和训练法律职业群体的法律思维, 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法律教育的重心放在培养和训练以法律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上。正如有位著名学者所说,“对于法律人来讲,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是有据(法律规定)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决定他们认识和判断的基本因素,况且非经长期专门训练则无以养成。” 因此,我们应改变原有僵化的法律教育模式,不能仅仅站在法律条文的角度上看法律,也不能过多的注重司法考试的普及,不能让法科学生只专注于司法考试的复习,不能忽视荒废对法律知识分析等能力的塑造和法治精神的培养,而应当立足于透过法律条文的表象,深入考察隐藏在条文背后的法律原则、论证体系和社会目的,对每一法律规则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从其缘起的条件、发展的历程以及根植的法律原则等方面着手,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确定当前选择这一规则的社会价值。 如此一来,这样的法律教育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易于认识、理解和接受,更为重要的是能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发现、学会符合自己探索法律理论最为重要的方法,进而形成一套独特的法律思维模式。
当然,在进行法律方法培养的同时,对具体司法实践的学习也不可或缺。知识并不等于能力,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核心在于实践。从目前我国法学院的实践来看,一般分为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三种。而作为国内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沈四宝教授提出在课堂上架起学校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三个桥梁。他指出“国内传统教学,分工较为死板,老师们不能参加实践”。因此,他鼓励法务实践,通过创设事务所支持法学教师加盟,可帮助教师创收,更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大量一线实践案例。同时,他又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事务实践,从课堂上的模拟仲裁庭和模拟法庭,发展到参与到现实中涉外贸易案件的仲裁。这样一来,活生生的案例令知识传授不再机械呆板,在讲授债务抵销权问题时,教师们直接剖析真实案例,学生们对违约和抵销的理解就更深了一层。通过多种形式的具体的案例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法律概念、法学理论,而且直接训练法律人的法律方法及法律的运用能力,让其亲身体验法律思维的全过程,为法律思维的培养提供有力的帮助。
创新现代法律制度作为法律思维的制度保障。现代法律制度为法律人法律思维提供规范依据。法律人法律思维的培育需要法治环境的保障,而法治环境的建构需要由现代法律制度来维护和完善。制度是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石,没有现代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法治坏境。而法律人法律思维的依据在于现行的法律制度,它规定法律人如何去进行法律思维,在什么范围内、用什么方法、行使权力的限度等等。这同法律思维的内涵是相统一的,法律思维强调尊重法律的思想观念,要求高度重视法律制度规范作用。这是法律思维作为制度之治中一个重要内容而具有的普遍性、原则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正好为祛除制度性障碍提供最有力的思维支持。
纵观我国的几千年封建制度历史再到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作为封建传统中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和公权力滥用的现象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由此而发生的对峙与碰撞从不停止,此类的新闻报道更是不绝于耳。“中国传统伦理重在‘亲疏有别’,以‘礼尚往来’作为人际交往的原则。一体遵循的法律在传统伦理面前碰壁,在互惠原则织起来的关系网前软化。不清除与法治相悖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与行为方式,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具有的技能与伦理,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扎根成活。”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直接影响正常的社会治理,直接限制法治社会的建构,甚至阻断了社会的发展,更有可能让其倒退几十年。因此,为了适应法治社会建构的需要,我们应当在法律制度更新、法律体系重构、法治价值转换等诸方面,全面确立现代法律制度,从而为形成法律思维提供规范支持和价值引导。用传统的办法显然难以为继,用体制内的思维解决体制内的阻碍只能是事倍功半,最好的选项就是引入法律思维和法治模式——通过法律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分配、制约和监督权力方面,由法律充当最权威的裁判员,实现权力从行政到法律的分流与转移,运用法律解决权力定位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法理学中抽象的法律思维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和体现,是从作为法律人的角度来发现、观察、分析、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命题。法律人的法律思维的展示是司法亲和力在社会传播中深层次的延伸,是当前落实十八大关于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论述的具体实践。通过法律人的法律思维的培养,使法律职业群体,甚至是社会公众形成法律思维的共识,最终达到进一步确立法律思维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实现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亲和力,进而推进法治社会建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