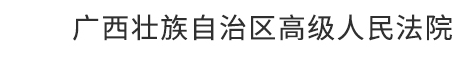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式建立始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2]各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该协议于2005年1月1日生效。该协议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基础,根据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3]的特点,就适用的争端的范围、磋商的程序、仲裁庭的设立、组成、职能和程序、仲裁的执行、补偿和终止减让等问题做了相应规定,为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和贸易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起到重要的促进和维护作用。随着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4]潮流的发展,有许多学者[5]提出,CAFTA争端解决机制也应顺应此潮流,强化司法化,修改机制中的不足。由于 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广受赞誉,因此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试图分析 CAFTA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化是否可行!
一、比较不同
CAFTA争端解决机制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设立,两者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CAFTA自身的特点,所以两者也存在许多不同,最主要的表现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体现出强烈的“司法化”倾向,而CAFTA争端解决机制只是具有“准司法化”的特征:
1、WTO争端解决机制设立了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SB).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简称DSU)规定[6],DSB负责执行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它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常设上诉机构的报告、监督裁决及建议的履行、授权中止减让;向WTO有关理事会和委员会通报与各适用协定有关的争端的任何进展;在DSU规定的时间内举行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经常会议。而在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争端解决机构为仲裁庭。仲裁庭是为解决争端而设立临时性的机构,其并不是一个常设的争端解决机构。在争端发生后,起诉方要求被诉方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争端时,由争端双方共同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此次争端解决完毕,仲裁庭即解散。[7]
2、WTO争端解决机制确立了反向协商一致原则。根据DSU的相关规定[8],在专家组成立、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及授权中止协定项下的减让和其他义务等问题的决策上,除非DSB经协商一致不通过该报告,否则,该报告应在DSB会议上予以通过。由于实行了“反向协商一致”,相关问题的决策几乎可以自动通过,因此反向协商一致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准自动通过程序,避免成员国采取拖延措施,大大增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和效率。CAFTA争端解决机制实行的是多数决原则,即仲裁庭应基于一致作出裁决,如果仲裁庭不能取得一致,则应按多数意见作出裁决。[9]
3、WTO争端解决机制设立了专门上诉机构。常设上诉机构由DSB设立,成员由DSB任命,受理对专家组案件的上诉。常设上设机构由7人组成,任期4年,可连任1次,其中3人应同时受理任一案件的上诉。[10]上诉的范围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做的法律解释。常设上诉机构的设立,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更接近于国内法的司法程序,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也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最突出表现。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则没有关于上诉程序的规定,其仲裁裁决是一裁终决,具有终局性,对争端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11]。
4、CAFTA争端解决机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都有关于拒不执行裁决的成员国的惩罚机制,但关于惩罚水平的规定不同。DSU规定[12]DSB授权实施报复的程度,应当与利益丧失或损害的程度相当。在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对惩罚水平没有作出明晰规定,报复水平是由仲裁庭根据“适当”原则决定的[13]。
二、是制度缺陷吗?
针对上述不同,有学者[14]总结CAF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其中包括没有常设仲裁庭、仲裁表决方式存在不足、仲裁复核程序缺失、惩罚机制不力等等,建议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司法化”规定,修改CAF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上述制度缺陷,以适应世界上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潮流的发展。可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发展真的就是一往无前吗?过度强调“司法化”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WTO争端解决机制有两个问题是一直备受诟病:
1、报复措施实质上的无力。WTO争端解决机制虽规定了报复措施,但报复水平仅限于与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水平相当。实际上这难以发挥报复对败诉方的威慑作用。当实施违法或不当行为获得的利益大于此违法或不当行为所导致的报复时,败诉方极可能无视报复,拒不改正违法或不当行为,宁愿接受报复,这是利益权衡的必然结果。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措施作为一种自力救济手段,其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端双方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当他们败诉时,他们要面对强国的制裁和压力;当他们胜诉时,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对不愿意履行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或报复。更多的情形是,弱国出于长远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考虑,而放弃采取报复措施。这种背景下的所谓正义,不仅不能使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争端得到公正处理,还有可能成为限制弱国发展的“枷锁”。
2、争端解决时间冗长。虽然DSU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争端解决各阶段的时限,但实际上关于时限的规定并不能得到完全地遵守。在《WTO争端解决规则与中国的实践》一书中,作者通过分析1995年至2004年DSB受理的争端,计算一个案件从磋商开始到DSB通过上诉机构报告的平均约700天,如果还要继续下面的程序,从DSB通过上诉机构报告到起诉方获得报复授权约需要700天,即从最初提出磋商请求到获得报复授权平均要4年时间[15]。
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化,依靠明晰的规定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有助于争端解决的公正、合理、权威,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但是由此带来的的弊端同样不容忽视。Karen J.Alter通过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分析,尖锐地指出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程度加深,会引起南北矛盾的加剧[16]。如果不考虑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中的弊端,不考虑中国与东盟自身特点和现实情况,盲目追随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恐怕出现欲速则不达的情况,不利于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因此前文中提到所谓的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缺陷,在笔者看来,值得商榷。
三、理性选择
如前所述,CAFTA争端解决机制实际上已具有司法化的特点,例如,规定通过仲裁解决争端,仲裁庭裁决具有终局性,对争端各当事方均具有约束力;规定了相应的报复措施等等,只是其司法化程度不如WTO争端解决机制高,CAFTA争端解决机制没有选择强化司法化,而是以仲裁为核心,强调磋商作用,综合选择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是法律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笔者认为,这是有其充分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
(一)从自身特点看,CAFTA是在东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东盟形成了“东南亚特色的决策方式”,即东盟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和国力强弱,在东盟事务的决策过程中绝对平等,使东盟成为一个以相互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共同利益集团。因此东盟一直没有设立强制性的组织机构,只是一个松散灵活的决策机构,决策中实行全体一致的决策原则和不干涉内政的组织原则,该模式被称为“东盟”方式。新加坡前外长贾亚库马尔曾对“东盟方式”的内涵作出过精辟概述:“东盟方式强调非正式、最小组织主义,包容性,强化磋商达到一致,最终和平解决争端” 。[17]这种历史的惯例从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实际使用情况可明显看出来。CAFTA争端解决机制自2005年1月1日设立以来,至今已八年多,没有一个成员国启用过该争端解决机制。即使有贸易纠纷,双方采取的都是国内救济措施,如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丙烯酸酯反倾销案、菲律宾与中国三磷酸纳反倾销案,最终都是由各国的商务部门作出反倾销裁决结案[18]。 虽然CAFTA争端解决机制从未被使用过,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与东盟经济往来的迅猛发展。自从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来,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200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547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双边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19]。
(二)从现实情况看,东盟的建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的戒备。今天,东盟对中国的戒备仍然存在,东盟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经济实力悬殊,而更多情况下,强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会让强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例如,报复措施的使用,经济实力越强的国家越无惧这种报复,而经济实力弱的国家即使被授权报复,也常常无力报复,甚至放弃报复。如果过于强化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有可能引起中国与东盟的矛盾,使东盟的戒备之心更重,反而不利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三)从强化司法化的要求而言,强化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成员国之间有广泛的社会共识,能够适用统一的规则。CAFTA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就目前而言,难以制定统一且完善的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WTO争端解决机制,因为设计的程序愈加复杂、解决争端时间过长等,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而被学者称之为“富人的俱乐部”[20]。DSU对各阶段程序的时限均作了规定,从成员一方投诉到上诉机构的报告通过,需要420天。何况,如前文提到的,实际上DSB在处理争端时往往不能充分遵守相关时限规定,所用时间远远超出规定的时间。这样庞大的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国家而言,往往是难以承受的。而在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因为采用的核心程序是仲裁,一裁终局,依据争端解决协议的相关规定,从成员一方投诉到裁决的作出,只需要187天。
有学者认为,“自由贸易规则若无制度上或章程性的保障辅佐,就不会持续有效”[21], CAFTA争端解决机制应当顺应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院化和法律化的趋势,成为中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22]。对此,笔者表示认同,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强化司法化并不适合目前的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这也是本文要强调观点。没有任何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任何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必须有利于成员各国的长远利益,关键是其合理性和现实性。在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背景下,在特别强调成员国之间平等合作、互不干涉内政、通过政府间的协商一致来解决争端的情况下,CAFTA争端解决机制既规定磋商、调解、调停的自愿解决方式,也规定仲裁这种强制性、有拘束力的解决方式,体现了自愿、协调和自我约束的特点。整个机制灵活、公正、高效,这既充分考虑传统因素,又弥补了传统方式的不足,同时又兼顾到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导向” [23]和效率性。所以,目前而言,现行的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1] 、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争端解决机制的简称。
[2] 、1967年8月8日,东盟正式成立,成员国有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加入。1995年7月,越南加入。1997年7月,缅甸、老挝加入。1999年7月,柬埔寨加入。至此,东盟发展成为囊括东南亚10国家的地区性国际组织。(陆建人,《东盟的今天和明天——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始建于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它是仅次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人口最多且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4] 争端解决机制采取一种类司法体系治理模式,即通过设置明确的条约与协定作为第三方受理投诉、评审违规行为、发布约束性制裁甚至授权报复。学者们将这种治理模式称为国际机制的司法化(legalism)。(苏瑞娜,“国际机制司法化治理模式的失灵-基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进程的分析(1980-2010)”,《法政探索理论月刊》,2013年第07期,第79页)。
[5]宋锡祥、吴鹏,“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完善”,《时代法学》,2006年10月第4卷第5期,第94页。
张昕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仲裁机制研究”,《河北法学》,第28卷第6期,2010年6月,第175——181页。
谷婀娜,“试析CAFTA下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公民与法》,2012年第4期,第62-64页。
刘付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初探”,《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第51-55页。
韦进深、王畅,“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当性及其意义——法律化的视角”,《毕结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31卷(总第155期),第124-128页。
[6] DSU第2条第1款规定,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负责执行规则和程序以及有关协议中的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但有关协定中另有规定者除外。因此,DSB应有权成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履行,并根据有关协议授权中止各项减让和其他义务。第2款规定,DSB应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理事会和委员会通报与各个有关协议之条款相关的各项争端的进展情况。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第6条仲裁庭的设立、第7条仲裁庭的组成。
[8] 具体规定详见DSU第6条第1款、第16条第4款、第17条第14款、第22条第6款。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第8条第5款:仲裁庭应基于一致作出裁决,如果仲裁庭不能取得一致,则应依照多数意见作出裁决。
[10] 具体规定详见DSU第17条。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第8条第4款:仲裁庭裁决为终局,对争端各当事方有约束力。
[12] DSU第22条第4款规定,由DSB授权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的中止范围,应和利益丧失或损害的范围相同。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第13条第4款规定,中止减让或利益应限于在〈框架协议〉项下、未能使被认定与〈框架协议〉不一致的措施符合仲裁庭建议的争端方所享有的减让或利益。
[14] 宋锡祥、吴鹏,“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完善”,《时代法学》,2006年10月第4卷第5期,91页。
[15] 纪文华、姜勇,《WTO争端解决规则与中国的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98页。
[16]苏瑞娜,“国际机制司法化治理模式的失灵-基于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进程的分析(1980-2010)”,《法政探索理论月刊》,2013年第07期,第80页。
[17] 王春捷,《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29页。
[18] 孙志煜,“区域经贸争端解决的制度与实践”,《法学评论》,2011年。
[19] 柳晖,“合作共羸: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与启示”,《东南亚之窗》,2011年第2期(总第16期),第10页。
[20] 蒋德翠,“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与实践”,《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119页。
[21] 赵维田,《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22] 衣淑玲,“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8月,第8卷,第4期,第50页。
[23]西方学者所说的“规则导向”方法,就是通常所指通过仲裁和法院解决争端的法律方法。(曾令良、饶戈平,《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